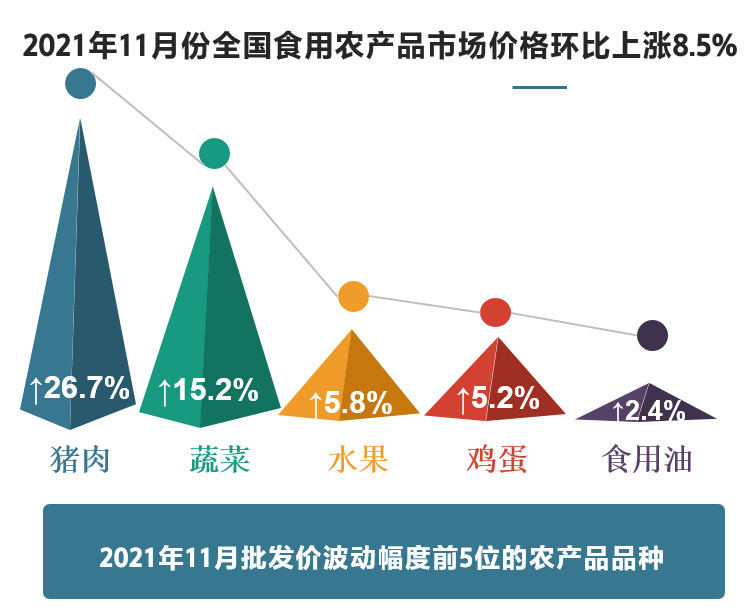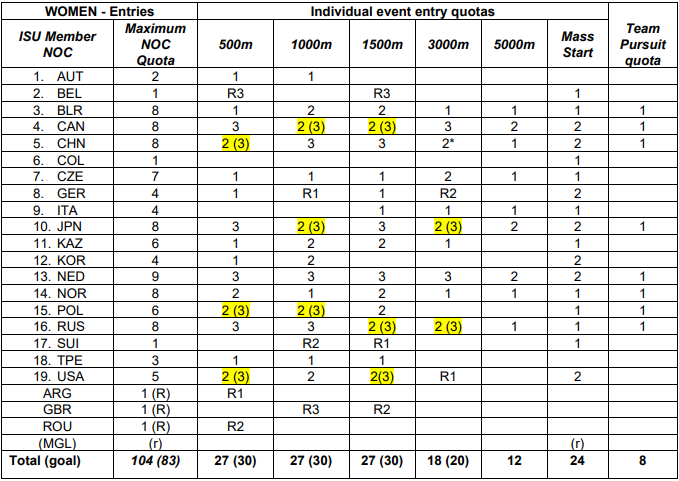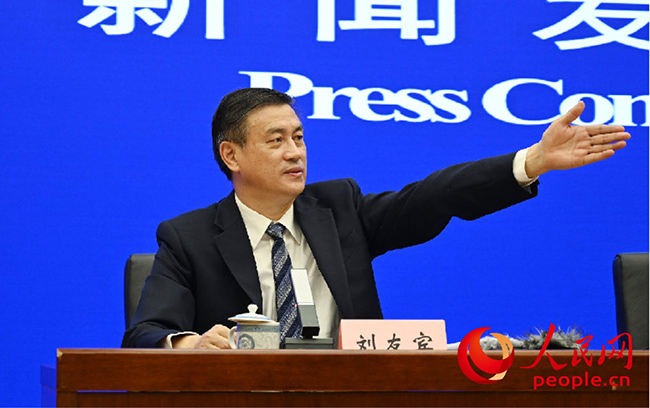我们对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选举投票率和选举制度研究发现,近年来,投票率下跌已经成为国际普遍现象。与全国性选举相比,地方性选举的投票率尤低,纽约、洛杉矶等金融中心城市的地方选举投票率在20%左右,一些大城市投票率仅为个位数。学者研究认为,投票率与选举的正当性(认受性)没有必然联系,投票率低不一定意味着选举正当性(认受性)低。美国两党近年来在投票率问题上取态相反、斗争激烈,近期的“民主峰会”进一步暴露了美国在选举投票问题上的政治两极化。
事实证明,投票率是西方民主的一个游戏,实质是最终赢得选举、获取政权的工具;投票率高低从来不是其选举的关注重点,赢得选举、维持执政地位才是关键。在英国殖民统治下,香港没有真正意义的投票权可言,回归前的香港所谓“选举”制度不存在投票率问题,通过操弄选举获取最大政治利益才是英国的目的,企图借此阻碍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并实行有效管治。
一、低投票率是近年国际普遍现象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全球平均的选举投票率已明显下降。以美国为例,其选举投票率近年已下跌至经合组织国家中的倒数几名。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投票率一般只有40%,而党内初选的投票率一般只有25%到30%。
与全国性选举相比,地方选举投票率通常更低。2021年11月美国纽约市(总人口约800万,与香港相若)地方选举(包括市长、市议会议员)中,投票率仅为24%,在490多万登记选民中,投票人数不超过130万。2017年的纽约市长选举投票率为21.7%。2017年洛杉矶市长选举投票率是20.1%,2013年是23.0%,2009年仅有17.9%。2019年芝加哥市长选举投票率为32.8%。美国南方最大城市达拉斯2015年地方选举投票率只有6%。加拿大多伦多、温哥华、蒙特利尔近年地方选举投票率大都为约40%。
西方很多地方选举投票率低,其原因往往是缺乏党派竞争,候选人之间观点接近,难以激励选民投票。西方学者认为,除非出现丑闻或重大举措,否则地方政治大多处于“平衡状态”,激发不出选民的投票兴趣。
二、投票率与选举的正当性(认受性)没有必然联系,投票率低不一定意味着选举正当性(认受性)低
美国等国的选举法没有规定任何最低的投票率门槛作为选举成功或者认受性的条件。西方学者认为,无论投票率高低,产生的投票结果不会有什么两样,低投票率不会产生不公平、不公正的选举结果。美国有1.6亿注册选民,如果从中随机抽取的1.6万人刚好能代表全国选民构成情况,那么这场选举就已经有了准确的结果和正当性。对同一个选区,70%的投票率和50%或30%的投票率往往有相同的选举结果;达拉斯市6%的极低投票率也不会被认为威胁到选举的正当性。低投票率的选举并不一定缺乏代表性,而应关注投票率的构成,而不是投票者的规模。不投票也是一种选择,说明那些不投票的选民同意由那些积极投票的选民代为选择政府领导人和代议士。
学者认为,不应为了提高投票率而推动那些无助于实现选举功能的选民投票。对于那些通常不投票或没有投票倾向的人,他们投票可能仅仅因为受到强迫,而与实现选举功能无关,这种情况下,投票率低反而不是坏事。
关于投票率与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之间的关系,尽管美国选民在地方选举中的投票率远比联邦选举低,但美国盖洛普公司、德勤公司多年调查都显示,美国人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反而长期高于对联邦政府的信任。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地区)遇到重大挑战,面临艰难抉择,才会出现创纪录的高投票率。例如,美国2020年大选投票率(66.8%)创1900年以来新高,就是因为美国面临多方面严重困难。当社会发展平稳,选民对未来有较好预期,没有通过投票来改变政府政策的强烈愿望,对选票就不会看得很重。投票率不高反而表明选民对政府施政和现状基本满意,感到不需要通过选举实现大的改变。
三、美国两党在投票率问题上的斗争表明投票率高低从来不是其关注的重点,赢得选举才是关键
美国民主党一直自称代表基层、弱势群体和劳工阶层,一直致力于提高投票率,降低投票门槛,尽可能把少数族裔、新移民、年轻人等群体都变为选民,并尽可能方便他们投票。投票率越高,民主党获胜的可能性越高。他们指责共和党故意使投票变得困难。共和党人则表示,他们反对投票改革是因为担心选民欺诈,指责民主党让自己的选民自动登记,提高民主党的投票率,而不关心选票的诚信性。61%的美国人认为,如果改变选举规则,使登记和投票更容易,不会使选举更不安全。大多数共和党人则认为,如果改变投票规则,使投票更容易,会降低选举的安全性、可靠性。
特朗普2020年公开指责民主党,称如果实行民主党推动的扩大选民投票的举措,“将永远不会有一个共和党人在这个国家当选”。实际上特朗普承认了当美国人民更多参与投票时,共和党就会输。他知道压制投票是他和共和党获胜的唯一途径,更高投票率只对民主党是好事,对共和党却不利,共和党只能依靠较低的投票率获胜,因此必须尽力压低投票率。
无论民主党如何想方设法提高投票率,或者共和党如何竭力降低投票率,他们真正关心的从来不是投票率,其最终的唯一目的都是赢得选举。只要能赢得选举,可以不择手段鼓励或者限制投票、提高或降低投票率。赢得选举、取得政权才是关键,投票率必须为此服务。
刚刚结束的“民主峰会”上,美国总统拜登提出“捍卫自由和公平的选举”,大力推动关于投票权改革的法案出台,旨在使投票更容易。这两个法案在共和党人的坚决反对下,一直无法获参议院通过,而共和党控制的19个州的立法机构已经以防止选举欺诈为名通过了限制投票的法律。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认为,在美国,投票本身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的党派分界线,大多数民主党人认为投票是一种权利,而大多数共和党人认为这是一种特权。皮尤中心调查发现,有3/4的特朗普支持者拒绝接受拜登作为合法的美国总统,他们支持特朗普对2020年大选投票存在广泛欺诈的指控。2021年11月,国际民主和选举援助研究所首次将美国列入其“民主倒退国家”名单,认为美国民主的明显恶化,表现在对可信的选举结果提出质疑的趋势增加,努力压制选举参与,以及失控的两极化;在没有任何欺诈证据的情况下美国出现对2020年的选举进行暴力抗争,这已经以不同的方式在秘鲁和以色列等地复制。
美国媒体批评:“民主峰会”上拜登的讲话显得异常空洞,拜登并没有为改变国内的民主倒退做出足够努力,美国的民主正处于严重危险之中,而扭转美国国内的民主倒退对于保持美国在国外的民主“领导地位”至关重要;对美国民主的最大威胁来自于内部,这不是一个美国有资格向其他国家讲授民主的时刻。正如美国投票权组织“黑人选民重要”的创始人所说:“当拜登总统正在主持‘民主峰会’时,我们自己的民主就在这里崩溃。当你无法在国内保护民主时,你不能试图向全球输出和捍卫民主。当你自己的房子着火时,你不可能成为全球消防员和民主火炬手。”
四、在英国殖民统治下,香港没有真正意义的投票权可言
香港最早引入选举成分的公共机构是洁净局(市政局的前身),市政局的选举权范围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非常狭窄,只属于较富有及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士,草根阶层被排除在外。据估计,1979年香港约有44万人符合选民资格,但只有不足3.5万人申请成为选民,而其中更只有不足1/3会参加投票。1981年的市政局选举总投票人数只有6100多人,代表性非常有限。
进入20世纪90年代,香港“选举”制度一直并非由香港本土的政治力量所决定,英国等外部势力始终试图操纵香港选举制度。英国在香港殖民统治末期,别有用心地引入和扩大选举,目的是阻碍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并实行有效管治,延续英国的政治影响。回归前的香港“选举”制度从来都是西方势力利用的政治工具,通过操弄选举获取最大政治利益。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港澳研究中心)
《 人民日报 》( 2021年12月24日 03 版)